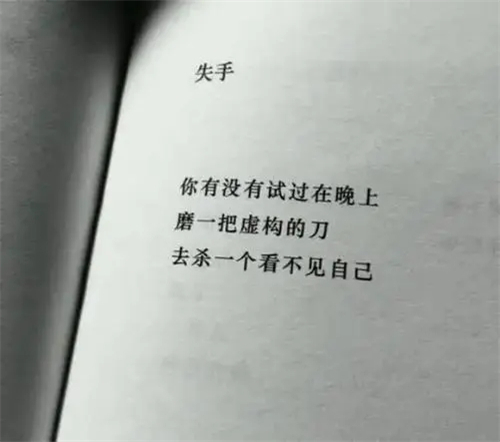前段时间,笔者一篇关于“死亡观”的文章,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大家对话题的讨论,意犹未尽,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经过学习与思考,笔者想再围绕这个话题谈谈。
诚然,就个体生命而言,世间诸事,以生死为大。每一个人,从娘胎出世呱呱落地,到长大安家立业,再到风烛残年结束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所以说,人生如“摆渡”,各有各的摆法,各有各的精彩。
人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生命体的存在过程。死亡,由于有着不可逆的严肃性,平日里人们对其有诸多忌讳。比如讲,我们许多宾馆酒店的房间号要避开“4”,车牌选号不愿选“4”。其实,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与不同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类部落最早对死亡的认识,始于对自然现象认知不足所产生的恐惧。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文明有了一定的基础,中国的思想启蒙开始活跃,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死亡观基本成型,其中又以儒家的死亡观对后世影响较大。它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超越死亡。这种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促使人们为民为国为他人而忠、孝、悌、友。孔子就曾站在岸边望着滚滚东流之水,发出“逝者如斯乎”的感叹,感喟“未知生,焉知死”,并推崇把有限的生命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认为思考生比研究死更有价值。
汉代是给国人生死观留下深刻影响的朝代。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靠着统治者的推崇,逐步在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上层社会的死亡观念,散发出了政治化的功能。统治者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考究死亡,定义死亡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当时匈奴人穷凶极恶的入侵,大汉王朝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家更需要“指导思想”和治理权力的高度统一与集中,所以,主流文化中突出的是为“集体”而献身的“仁人志士”。那时,整个国家提出了“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涌现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成就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在这种曲折和驳杂的阶级与民族矛盾的交合中,普通老百姓渺小而无助的个体生命,很难得到足够的爱护与尊重,他们只能把希望更多地寄托于来世。加上那些垄断宗教解释权的“劳心者”,添油加醋地塑造出了阎罗殿、地狱等各种关于死后世界的描述,鼓动活着的人要好好遵守道德规范,否则死后将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这套麻醉人的说教,虽然客观上对维护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作用,但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后世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汉代本身就是比较迷信的时代,出现了许多巫蛊事件。
应该说,中国人的死亡观,到了隋唐时期已经相对成熟。时人不大相信死后世界的说法,隋文帝坚决反对存在神仙怪异之类的说辞,唐太宗则把精力集中用在治国安邦方面。
进入近现代以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对外交往的增加,西方思想相继传入中国,也就有了“输入式”生死观,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逐渐为中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正所谓“地理是历史之母”,中国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地处亚欧大陆面向太平洋的中纬度封闭地带,这里虽然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息,物种丰富,但由于宜耕面积狭小、旱涝频发,加上受到毗邻游牧民族的冲击,所以惟有抱团实行“大一统”才能生存。从这一点来讲,新中国建立之前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历史现实,与大汉王朝前期的生存空间何其相似!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具有鲜明的“我为人人”的集体主义特性,有着中外以往任何死亡观所不能达到的境界,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生死观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可谓是“异曲同工”。这种死亡观传入中国之后,与儒家的思想相互融合,迅速找到了成长的土壤。
当然,传统文化今天依然有着历史传递的惯性。儒家除了通过功成名就来面对死亡外,还认同了另一条超越死亡的道路,那就是通过后代的香火延续来实现先辈未竟的愿望,达到光宗耀祖的目标。正如《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其实,所谓的香火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考究起来,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根本不可能存在某一历史族群或某一家族纯基因的传承,如历史上的中国,就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是一种文化认同。
也就说,我们今天提出来的人类传承,是对整体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而言的。就个体来说,我们必须立足于生而有所作为,同时又坦然面对死亡。死亡和这个物质世界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死亡的意义是推陈出新。人活着需要有生存的时空和消耗各种资源,如果人只有生没有死,地球哪能养活得了?最终只能走向自我毁灭。
由于死亡的不可知性以及世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再加上见证临死者的痛苦状态及死后的“狰狞”面目,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可怕的恐惧感。所以,我们的国家应该主动开展死亡观的教育。如何面对死亡,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生存方式。一个不敢面对死亡的人,是一个没有境界的人;同样,一个不敢面对死亡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
从死亡的社会属性来说,人的生命不是只有长度,还应该有宽度与质量。生命的长度可以适当延长,但哪怕你活到了一百岁,与宇宙的存在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的,而只有生命的质量可以不断地加密,增加其曾经存在的价值厚重度。提高生命的质量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简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联合体”,这是一种以追求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理想社会形式。所以,就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活着就要当好生死“摆渡人”,懂得“潇洒走一回”。至于怎样才算“潇洒走一回”?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有着不同的追求和活法。对共产党人来说,把有限的一生投入到为社会服务中去是自身信仰的要求。如果是凡夫俗子,无法做到崇高与伟大,一辈子安份守纪好好地活出自我,也是一种最起码的生活态度。因为只有大家都做到这一点,社会才有和谐与进步可言。
更明确地说,我们强调生命的社会属性、追求生存的崇高,并不排斥生命的个人属性和死亡的平凡。事实上,生命首先属于个人,生命是每个人最可宝贵的财富,如果一个人没有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剥夺他的自由乃至生命。
这些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思想正在深入人心,成为了许多人的“初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年清明节,我们以国之名祭奠,向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幸罹难的人们致以最沉痛哀悼,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个体尊严与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也彰显了14亿人民集体情感释放背后的巨大民族凝聚力。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启航,愿我们的国家不断走向富强文明,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面与幸福地活着。
作者:黄仁兴